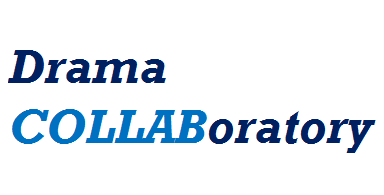03 Jan 對談:病理科 X 法醫面容辨識
對談:陳一云 和 嘉芙蓮.史密夫
嘉芙蓮.史密夫﹙Kathryn Smith﹚是一位視覺藝術家、策展人及法醫鑑證學家。她是斯泰倫博斯大學 (南非)藝術系的高級講師,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英國)的博士研究生;並於該大學的「面容實驗室」出任研究員,以及在「藝術在科學」 碩士課程中任教。 [i] [ii]
- A: 陳一云
- K: 嘉芙蓮.史密夫 (Kathryn Smith)
A: 非常感激你在百忙中仍願意和我一起踏上這探索的旅程!
K: 我很高興可以參與其中。自從去年在溫切斯特跟你碰面,我便對你的作品很有興趣。能夠參與你的展覽,其實是我的榮幸呢!
A: 我十分喜歡你的攝影裝置作品 「In Camera」(1) 很美的作品,也讓人在攝影、罪案、死亡、暴力及光各方面有啟發。從你的展覽專訪之中,你對身份、創作、死亡的再現以至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作「明室」﹙Camera Lucida﹚等的想法上的都令我產生不少共鳴。[iii] 當然我也很欣賞你近來的死亡面具研究。
有關時間和光,和你一樣,我也有參考「明室」這書。除了提及攝影和死亡的部份,書中還有一小段文字觸動我。
- 時間的雜音於我而言並不哀傷:我愛大鐘、時鐘、手錶,而且我記得最初的攝影器材屬於高級木器藝術工藝和精準的機械。說到底,相機是觀看的時鐘。也許,在我之內,有個古老的某某仍聽到攝影機器內木頭活生生的聲音。(巴特,1980,頁15)
之後我讀到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的著作,[iv] . 揭示了他從小想令時間停下來的慾望。 把時間捕捉,令其停頓下來;把光凝住,將之固定在某一刻,讓它不能熄去/漸滅……這些彷彿是人類基本的慾望,正是這些慾望激發了攝影的誕生。
或許我以時間為基礎的藝術形式(即劇場和音樂)的基因在作祟,我不禁疑惑,被攝影過程捕捉和壓縮的時間與光再次延展起來會是怎樣呢?
- 「在攝影上突顯兩個主題(基本上,我喜歡的照片都是以古典奏鳴曲的方式建構而成的)…」(巴特,1980,頁27)
如果時間和光以音樂、以奏鳴曲的方式去延伸,又會怎樣呢?
K: 我特別喜歡你引述巴特的文字。你所引用的並非那常被提及的「知面」和「刺點」的技術理論,又或者有關死亡,你所引用的反而是比較旋律性的部分,把這部分與音樂聯繫起來簡直是無懈可擊。當然,還有杉本博司的著作,以及他的個人收藏,都是與別不同的(見《Magnificent Obsessions: The Artist as Collector, Barbican/Prestel》﹙ Lydia Yee,2015﹚)。[v] 你提到的「時間」尤其重要,因為它是構成「光」的本質的一個部分。無論技術上還是理論上,作為一個喜歡把攝影解構的藝術家,我的理解是「光」與「時間」是互相連繫着的。我指的不單是轉瞬即逝與「凝住」兩者之間的關係——這只是攝影的一部分而已。 我並非一位物理學家,我對物理學的認識很不濟,如要把光與時間互相連繫的這個想法放在物理學的角度來闡述的話恐怕還有很多可以再說。此外,如果把音樂,或者其他表演形式一起思量的話,我覺得也就會建構了獨特的空間和時間。
對於這方面,你有一些看法嗎?
A: 我很喜歡你提及攝影和物理學中的光和時間。這令我想起我對黑洞的印象,其中的光、空間和時間交織著並壓縮於一瞬間。我常常覺得光是很吊詭的,光存在,並且無限穿越於外太空之中。光掌管了我們的視覺感官,主宰了我們對四周環境的體驗,但光卻無法獨立於空間而被經驗。光影空間成為一個緊扣的整體,這燃起我對光影空間的生命和自主性的渴望,從而引發我對時間的注視。光的旅程既是時間也是距離(想想「光年」這單位)。心的跳律、脈搏、呼吸、行走時的節奏 , 這些充滿韻律的時間是我們生命最直觀的部份,同時反映我們與生俱來對音樂的親切感。
在巴特所提及的古典奏鳴曲式中的三部結構及兩個主題發展的特質,似乎和不少的藝術或表演不無相似。或許,這種形式中的時間和兩個主題的發展是本能地反映着我們對生命流程的認知,那在「前攝影」階段的生命,那未被相機或死亡捕捉的時間?
K: 「藝術在科學」 的學生最近上了一課由一位天體物理學家所演講,有關於藝術與科學之關係的客席講座。這位天體物理學家在這一範圍很活躍,利用他的專業知識去參與一些計劃,而且經常與藝術家們互動。例如他曾經參與一個團隊,以深奧抽象的「暗物質」為題作園藝設計,並於修爾斯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奪獎。[vi] 天體物理學與園藝設計並非典型的合作領域,然而他們實在合拍地把一些複雜的概念深入淺出地介紹予門外漢。這位天體物理學家有關星雲及其他天體造像的討論,令我意會到這些宇宙性的暗物質及其他一切無形的,或一些我們未能驗證確實存在的東西之間是有所聯繫的。這就正是所謂的「隱匿」,從所見之影像中隱沒了。
對於以望遠鏡觀測星際,須輔以顏色濾鏡才能夠看到星體的「真」顏色,這著實令我很詫異;可是,令我更嘖嘖稱奇的是它們之間的規模。這些影像所展現的空間、距離和能量,這些構成生命的種種,其規模之大遠超我們的想像。然而,透過顯微鏡下我們卻能輕易地找到那些點點的光及流轉 的物質。它們與人的身體好像完全扯不上關係,這令我為自己與它們找定位時感到很掙扎。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說,極端的宏觀和極端的微觀,都是同樣地叫人難以掌握當中的「實體」,但這不代表抹煞了它們的「真」。可能我是一位現象學家,於我而言,空間、物件和環境當中表達情感的特質都令我找到不同的資訊及意義。
另外,對我來說,暗物質的概念與病理學起著直接的關係。那些沒有明顯外相的「無形的」疾病,於醫療影像裡會現身成為一些暗黑或空白的區域。視乎診斷/預斷如何,這樣的暗黑可能代表著某些情緒。要看到這些醫療影像,我們卻要透過不同的光譜,例如把這些光譜射穿身體,或者把別的訊號,如:超聲波、磁力共震等轉化成可見的光,並將之分析及詮釋。
我覺得把音樂創作的形式與結構加入一起考量極之有趣。因為除非我們按自己的喜好或特別的情況去傾聽音樂,否則一般來說很少會留意音樂的形式與結構的。如果我們有音樂的訓練的話,我們便可以解讀及詮釋一首作品,就像一位放射診斷學家單憑一張X光片,便能從灰濛濛的影像摘取大量的資訊。對於不諳這些專有知識的人,這些詮釋能力就像魔法,我們更會容許這種看似超自然力量的「魔法」當作臨床實證。西方文化尤其是持後啟蒙運動價值觀的人,皆把其信念放諸在科學,而非宗教當中。對我們大部分跟宗教避而遠之的人來說,這種對科學的信念,其實跟宗教信仰極之相似,情況就好比我們盲目地認定了許許多多的科技及流程,然後把我們的「信」,託付予權威與專家。
我亦不斷嘗試猜透現在超人文主義的各式念頭。這超人文主義,不但經常彰顯人與科技唇齒相依的關係,而且更要求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改造人的想法。我特別提出這些是關係到我們當代的經驗,特別在已發展國家,或多或少都會出現在生物與數碼兩者之間互聯的影響。我無意令我們的對話走進這個我也不太熟識的領域,但這些點子對我即將提出有關視聽媒介,甚至有些顛覆性的概念是很有用的前提。有關影像,特雷弗.帕格倫﹙ Trevor Paglen﹚提出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有關「視覺文化」這概念。[vii] 這是由於影像已愈來愈多是由,而且是為電腦所製造,根本是肉眼不能見到的。至於聲音,達蒙·克鲁考夫斯基﹙Damon Krukowski﹚曾製作一系列六個部分命名為「聽的方式」的播客。[viii] 他令我再三思考及明白一些我以前一直未能理解(或接受)有關數碼世界及數碼化的聲音的東西。
抱歉這段回應比較長,但很高興可以像這樣透過文字讓我的思緒馳騁及作出不同的連結,這些都是這個對話過程的得著。我們如能同步對話當然會很棒,但文字卻又可以帶出一些說話不能帶出的思考過程和連結。
A: 很感謝你慷慨的分享!我也覺得這樣的文字對話讓我有時間來回檢視自己的思緒,然後落實,感覺到思想上的煥然一新及進一步鞏固。
當我們在之前的電郵談到科學、空間和時間,「暗物質」一詞也在我腦海中浮現。「暗」對應「光」,一種基於光/可見度的分類。這種以光/視覺為主導的分類經常主宰着科學和醫學,西方醫學的發展便是建基於解剖學及病理學,兩種以人體可見的正常和異常為基礎的專科。一方面,即使我已經有十多年每天都觀看顯微鏡,我還是經常迷倒於顯微鏡下所見的一切 ——光綫穿透生命的切片再進入我的眼睛,既和諧且混亂。另一方面,我為視覺在醫學的主導甚至霸權地位感到不安。對於我這樣的一個病理科醫生/燈光藝術家,這是個奇怪的困境。
克鲁考夫斯基的播客、有關雜音的最後一部分於我而言是一個啟發。我也習慣從音樂及聲音出發及探索,而差點忘記了雜音。在數碼時代,雜音被壓抑甚至幾乎完全被消滅。可是,克鲁考夫斯基以小型獨立書店,並以和約翰·凱奇(John Cage)相遇時街上的雜音為例子,提醒我們雜音的重要性。(我這些思緒的流動可會是另一種「雜音」?)雜音的概念又將我帶到宇宙微波背景(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CMB)。CMB其實也是一種雜音,但這「雜音」能讓我們了解最接近宇宙起源的一剎那。除了CMB,宇宙還有其他的聲音、雜音和「合唱」。
這些宇宙的「聲音」並非我們平時所經驗的聲音,因為宇宙是接近真空,沒有足夠讓聲波壓縮傳播的物質。這些所謂的「聲波」其實是透過空間—時間連續不斷的擴張和壓縮而形成,例如兩個圍繞運行的黑洞之間的空間—時間的振盪。想著空間和時間的結合;聽到聲音和雜音,此時,宇宙的存在與所能被感受的體驗變得色彩繽紛,宇宙起源的一剎那變得活靈活現,這和平時以視覺主導所感受的「暗黑」宇宙有天淵之別。此刻,令我想起你提到撼動的聲音和視覺媒體之言——聲音和雜音成為聲響和視覺構作的對位。
CMB的雜音相信源自宇宙大爆炸後三十萬年的一刻,即約百億年前。這樣的時間維度遠超越我們的想像,聽來只像一堆數字。或許只有聲音、雜音和靜默足以表達這時間維度。
暫且不談難以言喻的宇宙時間維度,我近來被巴洛克時期及早期音樂所吸引,這類音樂所牽動的情感同樣難以言喻。有一首早期古鍵琴音樂尤其引起我興趣,這是由巴洛克時期德國作曲家弗羅貝爾格(Johann Jakob Froberger)所作的第二十號組曲,作品亦被稱為 「Memento Mori Froberger」。[ix] 源於原樂譜上的兩段題字:
「沉思我未來的死亡,緩慢且慎重地演奏,1660年5月1日於巴黎。」
及
「Memento Mori Froberger」
有一份音樂學研究文獻以當時法國流行的文學類型「虔誠的冥想」的概念去探討這首音樂作品,這文獻讓我更了解音樂和時間。[x] . 有一份音樂學研究文獻以當時法國流行的文學類型「虔誠的冥想」的概念去探討這首音樂作品,這文獻讓我更了解音樂和時間。 「敬虔式的冥想」像一個時鐘提醒當時的人們要在繁忙的日程中定時抽出時間去禱告及反思。(這和我們現代的繁忙生活似乎沒有兩樣,哈哈哈。)但在冥想當中,「時鐘」停止了,時間被凝結。透過時間的流轉和凝結,音樂作品中對死亡的沉思將不斷重複,不但在作品創作完成時展現,也在每一次演奏中循環。在音樂的沉思裡,讓時間沿着不同方向及不同速度穿越。
K: 哈!我唸高中的時候超迷巴洛克風格及中世紀的音樂。那時候,我對這些以及一些非西方的音樂的興趣都在加深。我覺得一些音樂類型,例如哥德搖滾都深受剛才提到的音樂所影響。當時我很喜歡的樂隊有許多,例如 Dead Can Dance 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正」。
「敬虔式的冥想」是很重要的概念。佛教及瑜伽的修行方式之所以能夠滲透到當代西方的生活中並非偶然。於我而言,在閱讀當中能找到一個靜止的平衡點很重要,而且很關鍵。創作時,我會有意識地嘗試達到這種靜止而平衡的狀態,把自己「將事情搞定」的慣性衝動制止,迫使自己「甚麼也不做」。這其實是很難的。但這樣把自己的行為一轉,例如我會聽一些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無關的東西,把焦點由所觀的改放在所觸的,是具有轉化作用的。或許,像我們這些在藝術和科學之間創作的藝術家,其實是在尋覓一個超越二元之光與暗的第三空間,例如在那能見的範圍及這個範圍以外,可會在那層次細微的光譜中找到這特別的第三空間?這正是我以前的作品「 In Camera」 嘗試探討的。這個作品不但希望突出光的展現以及遮藏能力,更加講及我們在視覺/能見的關係中的限制。光有一種獨特的個性,當它觸踫到物件與個體之後能將之轉化。我們的身體都有感光的潛能,只要我們暴露在或遮蓋於日光之中,我們的身體都會發生一些見到的及見不到的改變。當我每次忘記塗防曬用品,又或者當英國的不見天日的冬季影響著我精神與生理健康時,我都會想起這一點。我想起你對「前攝影」的評語,假如我們單從「以光書寫」的字義來看,我們能否想像出在照相機出現之前,有關攝影的歷史?
雖然我們並沒有特別提到死亡面具,但我們或可談談死亡面具如何有像照片般的功能作結。我的同事喬.希堅斯﹙Jo Higgins﹚曾參考巴特對攝影與死亡的微妙關係之論述而寫過有關亡者肖像的文章。她留意到:「如死亡面具一樣,亡者肖像是相中主角的物質痕跡。雖然相中主角已經不在人世,他遺留下來的痕跡卻永存。」(希堅斯 2012)
這裡的「物質痕跡」和符號學者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引的概念是相關的,意指一個客體直接遺留下來的痕跡。索引隱含著不存在的意味,它營造了一個或是物質性,或是視覺性的印記或痕跡,指示客體其實已經不再存在;又或者因為我們可以藉著遺下之物憑弔客體,所以我們已不需要他了。遺下的可能是一個腳印,一個指紋,又或者是在一些能引起化學反應的表面上,被光照遺下的痕跡(這是鑑證調查的原理,正如羅卡﹙Edmund Locard﹚的黃金定律:「人類無論做過何種接觸,一定會留下微物跡證。」)喬和我以前曾合作過一個名為《主體與客體之間:藝術與科學的接觸點上人類的遺留》的展覽 (Michaelis Galleries, 2014)。 我們除了透過攝影來闡述前面提及的觀點,更展出了一批解剖和病理博物館的生物及非生物的物件。[xi]
我們認為相片比較貼近「真實」的想法也是基於上述原因。但照片其實是一件混合物,它既包含著世上一些東西的痕跡,以光影將之印記起來;它也以影像和標記來代表那件東西。儘管許多人認為數碼影像不能具有索引性,但克莉絲.柏森 ﹙Kris Paulsen ,2013﹚ 卻很有說服力的反駁數碼影像是具有索引性的。[xii] 數碼影像與其指涉物(即照上呈現的影像)是受認知和文化所建構,並在物質的印記以外呈現更多複雜的訊息。
最近我很專注研究物質、非物質和象徵觀念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關係和其對照的影像所嘗試呈現的某種真實。這方面我發現卡亞.塞爾弗曼﹙Kaja Silverman﹚的《 The Miracle of Analogy: A History of Photography Part 1 》很有用[xiii] […] 她提及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提出有關攝影的進化理論:從一種具有證據般的真實的「工業」技術,以至一種以比擬手法來「透露」其對象的真實性,當中涉及兩者的互換性和關聯性。她觀察到:
班雅明提出攝影圖像的產生,乃受到一種神奇的意向性所驅使。這種意向性會朝向某一特定的外貌。它要先能讓人辨別,才能認乎所以。它更穿越了時間和空間,才形成這個樣子。當外貌形成的時候,奇妙的東西就會發生。「現在」於「過去」中發現,「過去」亦於「現在」呈現出來。(塞爾弗曼,2015,頁7)
我對於這樣的揭示潛能極有興趣。當中包括了信任、親密性、參與性和那些能衍生和激發的元素,就像你 (Amy) 的作品一樣。塞爾弗曼引用班雅明所著:「這不只是『過去』的光照耀到『現在』,又或是『現在』的照射在『過去』,而是當刻瞬間結集於閃光的剎那而形成的一個相互扣連的組合。」(塞爾弗曼,2015,頁8)
很精彩,不是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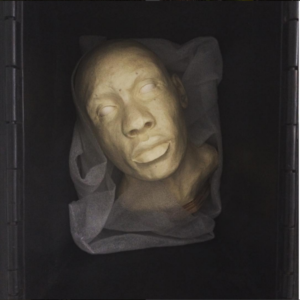 |
| 作品:Revealing l’Inconnue de la Seine, 2017
(相片提供:陳一云) |
作品:Detail of The Studio Familiar: X0198/1669, 2014, in storage.
聚氨酯頭骨鑄造,油性模型油灰,石膏,竹子,安裝在測量三腳架上 (相片提供:Kathryn Smith) |
中譯:譚尾卿、張潔盈、陳一云
原文為英文版(Link)
備註:
- Kathryn Smith的裝置藝術作品 In Camera (2007- ) 首展於 Goodman Gallery(約翰內斯堡及開普敦),並曾受邀於斯德哥爾摩的 Fotografins Hus 展出。此作品的另一個版本於2010年在莫斯科展出。
[i]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s Face Lab,
https://www.ljmu.ac.uk/research/centres-and-institutes/art-labs/expertise/face-lab
[ii] MA Art in Science of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https://www.ljmu.ac.uk/study/courses/postgraduates/art-in-science-ma
[iii] https://www.academia.edu/34879185/Kathryn_Smith_In_Camera_An_interview_with_Eva-Lotta_Holm_Flach
[iv] 現な像 – Utsutsu na zou (essays by Sugimoto in Japanese with photographs) Tokyo: Shincho-sha, 2008.
[v] https://frieze.com/article/magnificent-obsessions-artist-collector
[vi] https://www.rhs.org.uk/shows-events/rhs-chelsea-flower-show/exhibitors-old/archive/2015/gardens/dark-matter-garden
[vii] https://thenewinquiry.com/invisible-images-your-pictures-are-looking-at-you/
[viii] https://www.radiotopia.fm/showcase/ways-of-hearing/
[ix] https://open.spotify.com/album/2QdGJ0gBdlpcSZErtww9Hw
[x] Rebeca Cypess, “‘Memento mori Froberger?’ Locating the self in the passage of time.” Early Music, Vol. 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5-54. (https://academic.oup.com/em/article/40/1/45/402396)
[xi] https://www.academia.edu/22596633/_Between_Subject_and_Object_Anatomy_of_an_exhibition
[xii] Kris Paulsen, “The Index and the Interface,” Representations, Vol. 122 (Spring, 2013): 83-109.
[xiii] http://www.sup.org/books/title/?id=25116